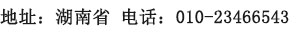6月6日,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成功出坞,取名“魔都”,代表它是“上海设计”“上海制造”的。或许“魔都”这一上海别称早已深入人心,但它诞生的历史还不足百年,年春,日本作家村松梢风乘船开启他的首次上海之旅,并于年将其旅沪见闻集结出版,取名《魔都》,关于上海的“魔都”意象由此在日本知识分子阶层传开。年后,这一源自日本的上海别称开始被国内学者所提起,之后随互联网发展得到了年轻群体的广泛认同和使用。
正如《魔都》一书中所介绍的那样,近代中日文人交流频繁,留下不少新闻和文学作品,构成我们了解上海近代史的一面镜子。近日,凤凰出版社推出《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后文称《魔都上海》)中文增补版,该书尤以近代日本文人对于上海的各种“记忆”为侧重点,阐论了上海之所以是“魔都”所具有的多面性,曾于年在国内首次出版。在村松梢风首次来沪一百年、《魔都上海》初版二十年后的今天,“魔都上海”这一城市意象,至今仍在为来自海内外的“魔都”观察者们提供着知识资源和文化灵感。
值《魔都上海》在国内再版之际,我们邀请到该书作者刘建辉老师,刘老师长期深耕中日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他将从自己撰写《魔都上海》一书的动机出发,带我们一同回溯“魔都上海”形成的历史。
(本期主持:陈虹静雯)
近期回顾
《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再版记
时隔近二十年,拙著《魔都上海》有幸在国内再版了。在此首先对凤凰出版社表示感谢。此次再版,是基于十几年前的日文增补版由甘慧杰先生重新翻译的。较之旧版,补充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及解放后的一些内容。就此,澎湃新闻约我能否谈谈感想。说实话,这十几年,上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身在日本,我已经很难把握其发展的时代脉络了。但盛情难却,同时作为原作者,也有义务对自己旧作的再版做一说明,所以只好勉为其难地重温一下当时写作此书的动机以及在书中阐述的一些观察与观点。
作为中国近代最早遭受西方列强影响的城市之一,上海自其开埠之日起,便不仅在中国内部,同时也在整个东亚区域内逐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内,近二百年来,它始终是一个连接内地与西方世界的窗口,对外,尤其是对于近邻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它亦曾是通向并接受西方的一个门户,而其后,则又转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与文化渗透乃至*事侵略的桥头堡。所以,正如我在本书的后记中所述,上海这一特殊的空间,是由内外两种文明与文化交织而成。具体地说,在近代史上,上海曾长期既部分地游离于内地的传统规范和西方的近代秩序之外,又部分地兼具着各自的规范与秩序。正是来自内外这两种“空间”力量的抗争与交融造就了上海独一无二的城市性格——摩登加荒诞的近代性。而日本作家村松梢风最早将其称之为魔都,亦无外是基于这两者间的一种“激烈”的结合。
19世纪70年代的南京路
对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生在东北,长在东北的我来说,当时的上海就是一个遥远的传说。还记得,每每有大量的上海知青从黑龙江路过我的家乡南下探亲时,他们那些“异样”的行为,诸如:嘴里会不时地吃着我们平日不见的奶油香糖,男女同学间肆无忌惮的热情举动,以及经常群体性地占据整个列车车厢等等,都会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尽管对其褒贬不一,归结起来却往往都用一个字来形容他们:洋!无需说明,这里的“洋”,即代表着远离我们的那个“西洋”,它是那个年代内地人望而不及的一种存在。有一次,家父通过关系搞到了一张每个中小城市只会分配到几辆的“永久”牌自行车购物卷,当这个上海产的宝贝被买到家里时,着实在邻里间产生了一次不小的骚动。大家纷纷来我家观看它的“伟容”,并不断地赞美其产地——那个洋气的大上海。而还是小学生的我,也因与上海有了一点“关系”沾沾自喜了许久。孰不知,这些少年时代的体验,日后竟成了我